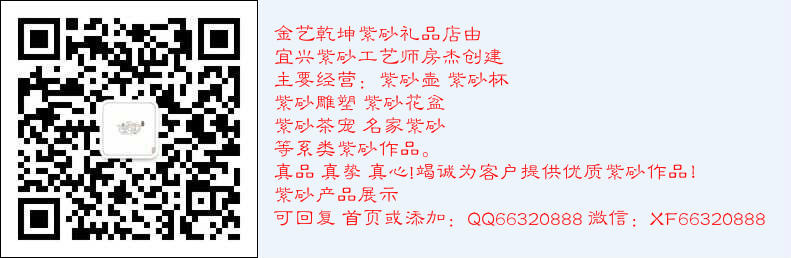蒋蓉原名蒋林凤,1919年生于陶都宜兴川埠潜洛六庄村的陶艺世家,11岁时随父母做坯制壶,20岁时应聘至上海,与伯父紫砂高手蒋宏高(燕亭)一起制紫砂仿古器。1941年时,应聘到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任工艺辅导,1944年受聘于上海虞家花园,设计制作各种花盆。1945年回乡制壶,1955年加入蜀山陶业合作社,制作国礼九件果品,1957年被评为“紫砂七艺人”(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之一。1978年被江苏省省政府任命为工艺美术师,1993年被国家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8年80岁高龄时还偶有创作。她的作品《荸荠壶》《芒果壶》分别被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香港茶具文物馆收藏。另一作品《枇杷笔架》作为国宝,被中南海紫光阁收藏。……

蒋蓉《百果壶》
紫砂真有秘笈吗?蒋蓉的回答是坦然的:如果说紫砂真的有秘笈的话,那就是在紫砂艺人心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工艺的一种把握,而不是固定的方程式或分子式,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语或解药;那是因壶而异的工艺理念,是不可复制的心得天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说来就来了,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在这十年里一直处于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然而,一路走来的中国紫砂在进人八十年代的时候,它的步履却还带着某种观望、拘束的迟缓。这里,我们不该忘记一位当时对紫砂走出国门起了重要作用的有识之士:罗桂祥。
罗桂祥是香港实业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此公名士风度,不喜欢灯红酒绿,爱紫砂却是成了癖的。别人金屋藏娇、三妻四妾,他平生只喜品壶、养壶、藏壶。为了收藏紫砂,他不惜荡尽家产。紫砂竟然如命根子不离须臾。一九七九年秋天,罗桂祥悄悄来到宜兴紫砂工艺厂,颇像一个探宝寻宝的侠士。他找了许多名手交谈,这里的人们还没有从“文革”的余悸里走出,说话都像温吞水不冷不热,让这个热心的香港人一时进退维谷。他听说大陆习惯用开会来解决问题,于是请求厂方召集包括顾景舟、蒋蓉在内的二十余名制壶高手开了一个“神仙会”。罗先生在会上拿出了一叠明清时期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等紫砂名家的作品照片,请在场的制壶名手仿制这些作品。有人就说,我们做了谁来买啊?因为当时紫砂的海外市场还没有开放,谁也不知道紫砂壶后来能比金子还贵。罗桂祥大声说,我来收啊!只要作品做得好,我出高价收购。他还要求制作者落上自己的款印,说这才是艺术品。就这样,罗桂祥作为“文革”后第一位推动并且订制紫砂高档产品的大客商、大收藏家而被写进了紫砂历史。在此之前,紫砂器均以品种来定价格,罗桂祥则开创了以制作艺人之名来定价格的规矩。这对推广紫砂,将其提升到与金玉比价的高级工艺品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在晚年蒋蓉的记忆里,当时她和罗桂祥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罗桂样笫一次上她的门来拜访,信手拿出一把陈呜远的调砂《席扁壶》请她鉴定,这是陈鸣远最具光货造型特点并显示非凡功力的作品之一。壶型极扁,适合冲饮绿茶。器型线面屈曲和谐,泥质用粗砂调制,配比恰当,肌理质感与形制十分和谐,目视有粗感,手抚则细腻。浑朴之中有峭拔之势。
蒋蓉一见它就觉得眼熟,仔细一看不禁有些激动起来,原来这壶竟出自她自己——四十余年前上海亭子间的林凤姑娘之手。当时虽然不能在仿制名人的壶上打自己的印章,但她在每一把壶的壶把下端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小小印记。生命如电如露,一切瞬间成空。这一把壶让蒋蓉感慨万端。世界就这么小,人生就这么巧合,全让一把壶收进去了。罗桂祥也兴奋不已,他执意要把这壶送还它真正的主人,而蒋蓉则坚持不肯接受已经属于别人的心爱之物。最后是蒋蓉以自己的一把小佛手壶与之交换,成为紫砂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桂祥的出现让蒋蓉获益匪浅。在他的大力推介下,蒋蓉的作品开始受到台湾、香港壶友的青眯。其时国门正渐趋开放之势,与大陆骨肉相连的台湾同胞陆续登岸,而紫砂壶则是同胞相会最好的媒介和礼物之一。台湾地区雨水充足,盛产高山名茶而茶道兴盛。
既有茶,岂可无壶?就是要用紫砂壶来泡,茶香才纯正。茶客与壶迷也由此应运而生。蒋蓉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和香港、澳门的主流媒体上,人们把她看作是横空出世的紫砂女艺人,她的田园式的清新风格使久居哺杂都市的人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然回归。人们相信她日后将是不可限量的泰斗式人物,因此,收藏她的壶,会比收藏玉器字画古董更有升值空间。
一些台港澳地区的壶商悄悄开进丁蜀古镇,他们找个小旅馆住下,一次次地上门拜访意中的紫砂艺人,先付下数目可观的定金,然后壶家会按照他们提供的壶样制作茗壶,这些壶商把壶带到台港澳地区出售,价格将是大陆上的十几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好的紫砂壶就是这样流向海外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大陆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富裕阶层,消费水平较低,好东西自然流向海外。一些穷了一辈子的制壶名家则在这个时期迅速发达,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他们一生的资本积累。
而蒋蓉却一直未敢造次,她觉得自己拿着公家的工资,却在家里卖自己的茶壶,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她老实了一辈子,她也不缺钱花。那些紧盯着不放的壶商便觉得这个老太太简直不可理喻。直至有人假冒她的壶出售,她才如梦初醒。时代就像一个魔术师,它总是在变幻着老实人搞不懂的魔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紫砂茶壶渐渐变得不仅仅是茶壶,它和字画、古董一样,潮涨潮落,可以把人推向天堂,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狱。
蒋蓉的一九八0年还有一件大事值得记述。这一年蒋蓉已经六十一岁,她身边一直无人,年纪一天天大了,确实需要有个人做伴,同时也可以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小勤是妹妹定风的孩子,以前经常来看她。有一次说到孩子的事,姐妹俩一拍即合,把小勤过继给蒋蓉当女儿。这是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端庄、淳朴、勤快,这一年才十六岁,但也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一年后,她中学毕业,厂里为了照顾蒋蓉,答应让她来厂里上班。从此,蒋蓉的生活里就有了一个贴心的女儿兼徒弟。小勤第一次跟着她的蒋蓉妈妈到厂里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为蒋蓉高兴。有人提议,既然做了蒋辅导的女儿,那就应该改个名字。叫什么呢?吕尧臣老师(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灵机一动说:“就叫艺华吧,你可要好好地把你妈妈的艺术才华学到手啊!”在旁的徐汉棠、汪寅仙老师(后来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都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勉励她早日成为一枝紫砂艺术之花。
华的到来确实给蒋蓉的单身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而且,做母亲的感觉让蒋蓉在日后的创作中不知不觉地平添了更多的儿女情长。艺华一边跟她学艺,一边照顾她的生活,空闲时母女俩出去散散步,一起学唱流行的新歌,艺华能够把一棵咸菜也烧得有滋有味,开心的日子原本就这么简单。时间久了,她在向外地来的客商介绍艺华时,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我女儿!”这时她就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女人。
一九八三年春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来宜兴主办陶瓷造型培训班,蒋蓉以六十五岁高龄成为该班年龄最大的学员。这个不脱产的培训班每天晚上上课,张守智教授清晰地记得,开班第一天晚上,蒋蓉第一个早早来到教室,她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张守智很敬重她,说:“蒋蓉老师啊,您是老前辈了,应该您给大家上几课才是。”蒋蓉说:“别客气了,张教授,我是真心来学习的。”
是的,黑板和粉笔字以及朗朗的读书声,一直储藏在她记忆的最亲切部分。女儿蒋艺华是这样回忆的:
她每天晚上把功课带回家,在灯下看书做笔记,到半夜还不睡。她说,人老了,课堂上讲的东西记不住,传统的老艺人只有实践,缺乏理论,眼界不免狭窄,怎么能创新呢?这些课程安排得真好,学和不学,真是不一样的。
理论培训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问,但对蒋蓉的创作,却有着较大的启发。她在多种场合说过,这三个月胜过一年呢。
综观蒋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壶艺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 以瓜果植物入壶入器: 花货肖形作品,大抵以神态见长,能否毕肖显神、工而不俗,当是工匠与艺术家的根本区别。蒋蓉以荸荠、百果、石榴、荷藕、寿桃、松果、西瓜、芒果、佛手人壶,无不体现出她的一片天真烂漫的情趣。壶外的蒋蓉大气素手,引一方天籁,点绛唇、藏温婉、锦绣深处更传淡泊;壶中的蒋蓉则如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她用一只稚嫩的小手牵引你,领向她梦境一般的田园,飘香的是瓜果,纷飞的是蝴蝶,高歌的是牧童,奔流的是清泉。你在这里找一找吧,那些失落的童真,忧伤的初恋,羞涩的少年梦……会重新叩访你的心灵。听,是蜀山古韵;闻,若蠡河潮声;观,乃烟雨幻化;品,化画溪月色。白发渔樵总是少,江南茶客依然多;何不共壶一柄,大雅紫砂而笑饮干杯耳?
2. 以动物入壶人器: 玉兔、春牛、乌龟、青蛙、蛤蟆、飞蛾、蝼蛄、螳螂……蒋蓉的壶艺创作,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点石成金的地步。一切自然界的生命,一旦被她看中,即可幻化今生,纵身一跃而成为小小精灵,被永远定格在紫砂艺术的天地之中。
3. 鼻烟瓶系列作品: 鼻烟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明末清初,鼻烟传入中国,鼻烟壶应运而生,它集书画、雕刻、镶嵌、琢磨等技艺于一身,不仅是盛装鼻烟的实用容器,更是供人玩赏和显示身份地位的艺术佳品。蒋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共创作紫砂鼻烟瓶、壶系列品种多件。其中,十件套葫芦形紫砂鼻烟瓶精巧华美,形象逼肖,紫砂陶刻名家谭泉海见之甚喜,应蒋蓉之邀,在每个鼻烟瓶上刻下明秀的山水、遒劲的书法、吉祥的动物以及古朴的瓦当纹样,使它们成为紫砂袖珍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他如荸荠、菱角、苹果、竹节鼻烟壶则玲珑小巧、实用耐看,令人爱不释手。
4. 陶塑系列作品: 蒋蓉的陶塑造型功力在同辈艺人中堪称一绝。其中莲藕笔架为文房雅玩,自是妙思若神、形色俱佳;陶土假山则有黄宾虹笔意,逶迤苍劲;水牛、狮子、老虎等动物陶塑,着力表现生命的伸展、张扬之美与动物的神态动感之美,以民间美术的鲜活意趣一扫学院派的拘谨之风。最具深意的是一件名为《邯郸梦》的冬瓜陶枕,色泽青碧,一端花蒂、一端瓜蔓,两端微微翘起,中间稍凹。陶枕乃我国传统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定窑孩儿枕尤为出众。蒋蓉创作的冬瓜枕自然舒展,无矫饰之态。著名画家程十发为之题名《邯郸梦》,取唐代传奇《枕巾记》中“一枕梦黄粱”之意,以冬瓜之清丽素朴醒人于俗世。陶刻名家谭泉海在枕上欣然命笔:“静坐书斋读文章,卧寝竹窗听秋岚。”
上世纪八十年代蒋蓉可圈可点的作品不胜枚举,如果让它们集合起来,简直是一个庞大的紫砂兵团。就像一部被打开的书,我们已经读到了它最精彩的章节。如果让蒋蓉自己来选择,在那么多爱不释手的作品里选出几件她最满意的,也许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但她最终还是会肯定地告诉你,《荸荠壶》和《西瓜壶》,还有《秋叶树蛙盘》《月色蛙莲壶》都是和她十指连心、与她的生命等量齐观的不可割舍的经典之作。
《荸荠壶》创作于一九八一年。一直到八十七岁的晚年,蒋蓉在叙述创作这把壶的过程的时候,脸上还掩饰不了孩子一般的得意:“说穿了吧,我这把壶就是做给那些看不起花器的人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顾景舟已经是当代紫砂的领军人物。他平时的言谈举止,总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对紫砂花货作品的轻视。蒋蓉的脾气,从来都是用作品来说话的。《荸荠壶》的壶身,是一件典型的光素器作品,而它的装饰却具有花器与陶塑兼工的特点。壶嘴与壶把的线条,如凌波仙子凭空一跃,有意想不到的洒脱与干练;而壶身的装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点缀。它已经逾越了像与不像的窠臼,那种草根而不卑贱、雍容而不显贵的气度,是需要一种气质来支撑的,一般的紫砂艺人怎可比拟呢?《荸荠壶》要告诉别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光素器与花器绝不是天敌,就像艺术不应有贵贱之分,而只有优劣之别;好东两不怕兼容,好朋友应该共存。《荸荠壶》最后被英国人永久收藏于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它代表中国,代表一个遥远的东方民族的工艺秘笈。
《秋叶树蛙盘》,一九八三年创作。秋天是容易让人感怀的季节。古人说一叶知秋,蒋蓉正是从一张卷曲的树叶造型人手,她设计了一只小青蛙,趴在树叶的一端,睨视着一只可怜的小小飞蛾。它们本是一对天敌,但青蛙发现,在深秋萧索的天气里,这只小小飞蛾就要呜呼哀哉了,小青蛙会怜悯它吗?它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易逝的悲哀?蒋蓉把所有的故事安排在一张树叶的时空里,接下去小青蛙和小小飞蛾之间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那肯定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了。飞蛾的命运牵动着蒋蓉的心。她爱这个弱小的即将离去的生命,她要赋予它以美丽,哪怕是短暂的一瞬。前前后后,她一共捉了一百多只飞蛾,放在小瓶子里观察临摹,她熟悉它们的每一根筋纹,她甚至能感受到它们的呼吸。最后的一只小小飞蛾就这样定格在树叶的底部,它是一只吟唱的蛾,周围蛙声如鼓,像十面埋伏;天已崩,地欲裂,它依然吟唱,永远吟唱。当它终于不再是活生生的飞蛾而已经是艺术品的时候,一位记者和它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在一个陶艺展览会上,记者用手去拍打它,以为它是偷偷跑进这艺术殿堂来的不速之客。它偷偷地乐不可支:“别怪我,是蒋蓉奶奶让我这般真假难辨的呀。”
《西瓜壶》,一九八五年创作。又是一件光器式的浑圆佳构。许多媒体在报道此壶时,着重强调了蒋蓉一连多日冒着烈日酷暑,不顾严重的腿疾,和女儿艺华赶了几十里地去西瓜地里写生的情景。但在蒋蓉晚年的回忆里,写生的经历只是一带而过,她说得最多的,是西瓜壶的表现手法。西瓜之圆,是圆润饱满之圆;西瓜之脆,乃清脆新鲜之脆;蒋蓉在泥料的配置上做了几十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表现西瓜的色彩语言。一次,我采访蒋蓉的时候忍不住提过一个问题:紫砂真有秘笈吗?蒋蓉的回答是坦然的:如果说紫砂真的有秘笈的话,那就是在紫砂艺人心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工艺的一种把握,而不是固定的方程式或分子式,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语或解药;那是因壶而异的工艺理念,是不可复制的心得天机,你只能在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语或解药;那是因壶而异的工艺理念,可不是复制的心得天机,你只能在具体的作品里寻找答案。把好东西用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是所有的艺术家毕生追求的目标。蒋蓉的《西瓜壶》花纹清晰可爱,瓜藤、瓜蒂塑成壶嘴壶把,从壶身与壶把的连接处斜出一张墨绿的瓜叶,两朵嫩黄的小花,呼应出一片鲜活灵动的气息。它永远像一首田园诗,在被千万次朗读后依然翠绿如生。此壶现藏于宜兴陶瓷博物馆。

《月色蛙莲壶》,一九八九年创作。这是一件段泥作品,以写实手法把自然界的莲荷、青蛙、昆虫集于一壶。原宜兴陶瓷博物馆馆长、紫砂文化专家时顺华先生这样评介这件佳作 :
:
她巧妙地利用藕节组成壶嘴,荷叶梗与花梗绞缠扭为壶把,莲蓬为壶盖,上栖一青蛙为壶纽,壶身为盛开之荷花,花脉清晰、自然灵动。童心和天趣是蒋蓉创作的主题,她具有捕捉美的瞬间的天赋才华,又有一手微型雕塑的过硬本领,善于把大自然中的美丽和生活中的情趣融入壶中,开创了独具风格的“蒋氏陶艺”。